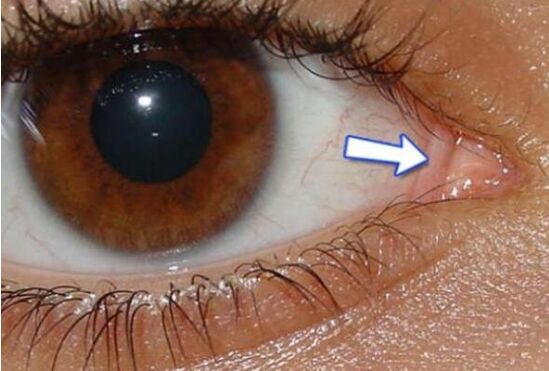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关于女娲信仰的起源地问题,学界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对于推进女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三皇、地位
和女娲造人和补天神话相比,女娲女皇之治神话的文学移位过程最为滞涩,无繁荣而近夭折。这一强烈的反差说明神话在其走向文学的移位过程中,其移位的程度是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限制和制约的。
在女娲神话中,有关女王之治的内容与其它内容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但记载的内容比较模糊。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当是著名的“三皇”之说。
例如东汉王符《潜夫论》说:“传说三皇五帝,很多人都认为伏羲神农合称三皇。其中一人或者说遂人或者说祝融或者说女娲。其中是与非可就不知道了。 ”说明东汉之前关于“三皇”的说法至少有三种。那么女娲缘何能够取得三皇的尊位,她后来缘何又被排除
三皇之外,这个变化与其文学移位的程度有何关联,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有关女娲为女皇的说法,现有较早的材料是西汉时期《淮南子·览冥训》说:“伏羲、女娲不设法律制度却以至高德性而流传后世,为何,是因为达到了虚静无为纯粹专一的境界,而不是忙于琐碎的政事。” 这里没有明确女娲是什么身份,但她能和伏羲并列,且属于能否“设法度”和“遗至德”的人物,显然已经暗示出其女王的地位。与《淮南子》大约同时代的《诗含神雾》的记载可为佐证:“含始 咽下红色的珠子,刻道:玉之精英生下汉代皇帝,后来赤龙感应女娲,刘邦兴起的原因。” 这个著名的刘邦诞生的故事似乎也暗示出女娲的至尊地位。
也许是还有其它亡佚材料,也许是根据以上材料的推测,不久就出现了对女娲是三皇之一的猜测和坐实。应劭《风俗通义》引用《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郑玄则明确指出女娲是三皇之一:“女娲,三皇承宓戏者。”这种观念到了南北朝时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女娲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约定俗成的女皇的符号或代称。
《北齐书》:又正好太后被幽禁了,祖埏想让陆媪成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的先例,为太姬说话。对人说:“太姬虽说是女人,但实在是英雄豪杰,女娲以来从没有过。”《祖珽传》
祖珽出于奉承的目的,将太姬比作女娲式的女中豪杰,说明女娲作为女皇角色在社会上的普遍认可。
唐代之前女娲能够取得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究其历史文化根源,在于原始母系社会女性崇拜观念的遗传。女娲造人造物以及补天济世的传说,都是其神话残余。而作为母系社会女性崇拜的极至,女娲进入“三皇”之列是合乎历史本来面目的。
甚至有理由作出这样的臆测,女娲当年在先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比人们当今的了解和认识要较高。对于甲骨卜辞中有关祭“东母”和“西母”的记载,过去一般将其解释为日月之神。现代有人从原始的二方位空间意识出发,将东母西母分别解释为女娲和西王母。从女娲在远古时期曾经有过的“三皇”地位和母系社会女神的普遍地位来看,这种说法是可以相信的。
神话的历史移位,照样需要适合的生存土壤。一个男权社会,尤其是儒家一统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可以有足够的力量让借助母系社会女权观念而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娲的女皇地位受到了质疑,并将其排挤出去的。
司马贞《补史记》:女娲氏也姓风,蛇身人首,有神灵的圣人品德,代替宓牺立号称女希氏。没有什么功绩,只有制作笙簧,所以《易经》不收录。不接应五运,一种说法女娲也是木德的君王。这是因为伏羲的后面,已经有好几代,金木轮番循环,转了一圈又一圈。特别推荐女娲把她的功劳抬高而充任三皇,所以并列(连次)木德的君王”。(《三皇本纪》)载。
鉴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之前历史的缺失,司马贞以《三皇本纪》为其立传。但其对三皇之一的女娲的态度,却是承袭了汉代以来对女娲这一女性神帝的冷漠和贬低的说法。一方面,他无法回避
前代母系社会有关女娲圣德传说的遗闻,承认女娲有“神圣之德”。另一方面,他却为把女娲排除三皇之外寻找各种理由和根据。首先,他对女娲造人、补天等人所共知的功德视而不见,认为女娲除了“作笙簧”之外,没有什么功德可言。并以此作为《易经》没有收录女娲事迹的原因。
其次,他还用秦汉以来的“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女娲被排除三皇之外的理由。按照他的解释,自伏羲后经过了数代,金木水火土五德循环了一圈,所以轮到女娲时应该又是木德。然而女娲无论是抟土造人,还是炼石补天,都显示出其土德的内质。所以女娲是“不承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