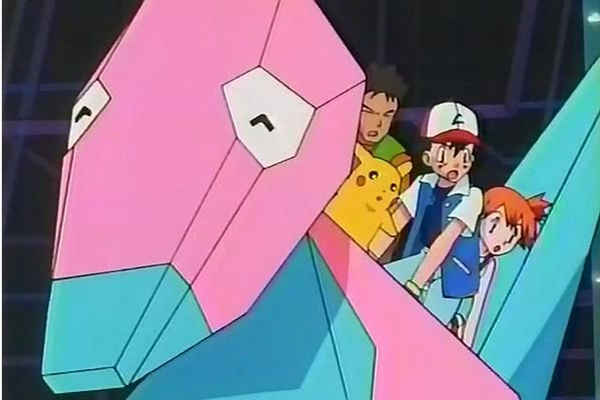这两位钱老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不仅归结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心中博大的理想,还要归结于他们兼融中西的学养。他们留学北美,在最崇尚科学创新精神的环境中广泛涉猎,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进行深入研究,这样的视野和积累,使他们对中国科技和教育的症结有了清醒的认识,荣耀的光环以及晚年平静的生活并没有减少他们为这个国家人才危机、前途命运的担忧。
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校长
钱老生前有二三十个头衔,从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到一般社会团体名誉职务,乐此不疲,操劳一生。2010年7月30日,钱老溘然长逝。我在乐乎楼协助宣传部同志接待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在底楼大堂遇见钱老的儿子元凯,向他表示了慰问,并说了一些记者采访的事情。谈话间,元凯充满感情地说:“我父亲生前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校长。”“在他去世前的27年里,他把上海工大及上大的师生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儿女,他的家就在上大。”
为了学校的发展,钱老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对师生的关爱是全身心、全方位的。
钱老到了上海工大以后,在学校里有一项教学活动是他亲力而为持续了好几年的,就是听老师讲课。他听课一般听一节,听完以后就提出意见。学校专业门类很广,课程很多,他会有选择地听。一年听几十节课,他都能提出一些意见来。后来,国务繁忙,他很少下去听课了,但他在学校时,总是喜欢到处走,到处看,也会不时地叫助手安排一些人来谈话。谈话对象有校、院、系领导,有普通教师,也有学生干部,谈话内容很广泛,既谈学校里的事,也谈个人的工作和思想。
钱老当校长,学生在他心目中占有最重的分量。他总想着,要把上大的每一个学生都塑造成:“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为此,他一生都在为创办一所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而努力;他亲自绘制新校区规划图,要给学生盖最好的校舍;他倡导“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三学期制),要为学生制定最自由的学习制度;他要求教师必须教学、科研双肩挑,首要的事是教会学生自学,要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担当责任。他的喜怒哀乐系于学生的每一步成长过程。
学校有两个大会,钱老是一定要参加的,一个是新生开学典礼,一个是毕业生典礼。按照他的说法,这关乎“学生人生的大事”。每次毕业典礼,他希望亲手把一份份毕业证书递到学生手里。学校规模大,毕业生多,发证的时间很长,但他总是精神饱满,脸上始终洋溢着笑意,是那种很惬意的笑。他每发一份证书,就要和学生握一下手。有时候,他会跟边上的人说上一句:“嗯!这个学生手心出汗,手冰凉,那是因为身体虚弱,缺少锻炼。”爱生如子,溢于言表。
学校每年要拍毕业照。在延长校区,若天不下雨就安排在大草坪,若下雨就在体育馆。钱老只要在学校,就会和学生们一起合影。有一次拍毕业照,在大草坪集合学生队伍时,并没有下雨,等学生全部站好队,只等钱老等校领导到位就可以拍了,不料,领导还未到场,却下雨了。负责这次拍摄工作的干部是位新任命的某部部长,他心想,雨不大,那么多人,排好队也不易,队伍就不要散了,等一等或许雨就停了。钱老从乐乎楼楼上下来,正要出门去大草坪,一看正下着雨,就停住脚步,可再一看,学生们正站在雨中,等他合影,顿时勃然大怒,厉声喝道,谁让学生们站在雨中的?是谁?要撤他的职!把这位年轻的部长吓得脸都变色了,赶快把队伍拉到了体育馆。
钱老怕学生出事,最不愿意看到学生因年轻犯错而受到过于严厉的处罚。1989年四五月间,在北京因胡耀邦逝世所引起的学潮骤然爆发,且愈演愈烈。到了5月中旬,上海也有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到外滩市政府大楼前静坐。上海工大也有学生提出要上街游行、要静坐、要绝食,偏偏这个时候,学校上级领导部门的表态却不明朗。面对这种局面,刚从外地回到学校的钱老非常焦虑,他一方面要求学校领导发动干部、教师做好学生的工作,尽力维持学校内部的稳定;二是指示自己的秘书联络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经过紧急磋商以后,以五位大学校长的名义给《解放日报》社送了一封致学生的“公开信”,呼吁青年学生冷静面对,停止绝食,呼吁中央领导及早与青年学生对话,使局面缓和下来。5月18日,《解放日报》以新闻稿的形式,摘要发表了这封信。客观地讲,这封信在当时的局面下起不了什么作用,事态的恶化早已超出了这五位校长善良的愿望,但见校长们终是担忧青年学子在风雨中折断翅膀。